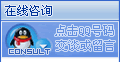| ГАҮш(guЁ®)‘—·ЁҪвбҢ·Ҫ·ЁЦ®ТӘЛШ·ЦОц |
| ЧчХЯЈә[·¶ЯM(jЁ¬n)ҢW(xuЁҰ)] |
ГАҮш(guЁ®)‘—·ЁҪвбҢҙуЦВҙжФЪЦшФӯТвЦчБxЕc·ЗФӯТвЦчБx»тХЯҪвбҢЦчБxЕc·ЗҪвбҢЦчБx·Ҫ·ЁЈ¬ТФј°ТБАыЛщЦчҸҲөД‘—·ЁҪвбҢЦ®өЪИэ—lөАВ·јҙіМРтЦчБxҪвбҢ·Ҫ·Ё��Ј¬ө«ҝӮөДҒнХf�Ј¬Я@Р©·Ҫ·ЁХ“¶јКЗҮъА@ЦшИзәОЦТХ\(chЁҰng)УЪ‘—·Ё¶шХ№й_өДЈ¬ЖдҢҚ(shЁӘ)Щ|(zhЁ¬)„tКЗИзөВОЦҪрЛщСФ��Ј¬ҢҚ(shЁӘ)лHЙП¶јКЗЎ°ҪвбҢЦчБxХЯЎұ�����ЎЈұM№ЬЛьӮғЦ®йgҙжФЪЦшУ^ьc(diЁЈn)Ц® Һ(zhЁҘng)Ј¬ө«ГҝТ»·N·Ҫ·ЁХ“өДұіәу»щұҫЙПҪФҮъА@Цш»щұҫПаН¬өДФӘЛШЯM(jЁ¬n)РРҪвбҢ�Ј¬Я@ҫНКЗЈә‘—·ЁОДЧЦөДә¬БxЎўБў‘—ХЯТвҲD�����ЎўЛҫ·ЁЕРАэәНғr(jiЁӨ)ЦөЕР”а�ЎЈИз№ыТФҙЛҒн·ЦОцГАҮш(guЁ®)‘—·ЁҪвбҢ·Ҫ·ЁХ“Ц® Һ(zhЁҘng)өД№ІПа�Ј¬„t•ю(huЁ¬)ЯM(jЁ¬n)Т»ІҪАнҪв·Ҫ·ЁХ“Ц® Һ(zhЁҘng)ұіәуҙжФЪөДҶ–о}ЎЈ
Т»����Ўў‘—·ЁОДЧЦөДә¬Бx
‘—·ЁҪвбҢ·Ҫ·ЁЦРҪӣ(jЁ©ng)іЈұ»Я\(yЁҙn)УГЕcҸҠ(qiЁўng)Х{(diЁӨo)өД·Ҫ·ЁҫНКЗФӯТвЦчБxЈЁoriginalismЈ©Ј¬Ф“·Ҫ·ЁХ“ЦчҸҲ‘—·ЁҪвбҢ‘Ә(yЁ©ng)®”(dЁЎng)°ҙХХ‘—·ЁЦЖ¶ЁЕcНЁЯ^•r(shЁӘ)өДОДЧЦә¬БxЈЁmeanings of wordsЈ©����Ј¬°ьАЁ‘—·ЁОДұҫОДЧЦөДФӯКјә¬БxәНБў‘—ХЯөДФӯКјТвҲDЯM(jЁ¬n)РРЎЈОДЧЦөДФӯКјә¬Бxұ»ФS¶а·Ё№ЩәНАнХ“јТӮғЛщҸҠ(qiЁўng)Х{(diЁӨo)�����ЎЈІ»Я^����Ј¬Я@·NҢҰ(duЁ¬)ФӯКјОДЧЦөДә¬БxөДЦчТӘі«Ң§(dЁЈo)ХЯИзІ©ҝЛәНЛ№ҝЁАпҒҶҪФЦчҸҲОДЧЦөДҝНУ^ә¬Бx»т№«й_»ҜөДОДЧЦә¬Бx�����Ј¬¶ш·ЗБў‘—ХЯөДЦчУ^ә¬Бx���ЎЈҢҰ(duЁ¬)ОДЧЦҝНУ^»Ҝә¬БxөДҸҠ(qiЁўng)Х{(diЁӨo)Ц®ДҝөДФЪУЪЕЕів·Ё№ЩөДӮҖ(gЁЁ)ИЛғr(jiЁӨ)ЦөЕР”аЎЈЦ®ЛщТФЦШТ•‘—·ЁОДЧЦөДә¬Бx����Ј¬ЦчТӘФӯТтКЗТт?yЁӨn)й‘—·ЁКЗіЙОД·ЁөдЈ¬КЧПҜҙу·Ё№ЩсRРӘ –ФЪ1803ДкөДсRІ®Ап°ёЦРҫНҢўЛҫ·ЁҢҸІйөДХэ®”(dЁЎng)РФҪЁБўУЪ‘—·ЁКЗіЙОДЦ®КВҢҚ(shЁӘ)Ц®ЙП��Ј¬јҙОТӮғ“нУРТ»ІҝіЙОД‘—·Ё��Ј¬ЖдОДЧЦөДә¬БxјsКшЦш·Ё№Щ����ЎЈҙу·Ё№ЩЛ№ҝЁАпҒҶТІЦёіцЈәЎ°ОТӮғЙъ»оФЪБў·ЁөД•r(shЁӘ)ҙъЎұЈ¬Ў°ГҝТ»ӮҖ(gЁЁ)УЙВ“(liЁўn)°о·ЁФәЛщҪвӣQөД·ЁВЙҶ–о}��Ј¬¶јЙжј°өҪОДұҫөДҪвбҢ�ЎЈЎұ
[1]ФшИОГАҮш(guЁ®)Лҫ·ЁІҝйL(zhЁЈng)өДГЧЙӘХJ(rЁЁn)һйЈә‘—·ЁҪвбҢөД·Ҫ·Ёй_КјУЪОДјюұҫЙн����Ј¬іЙОДОДјюҫНКЗјЩ¶ЁЛьДЬӮчЯ_(dЁў)ә¬Бx�Ј¬ОТӮғЦӘөАДЗР©ЦЖ‘—ХЯЧРјҡ(xЁ¬)өШМфЯxЛыӮғЛщК№УГөДОДЧЦ�����Ј¬ЛыӮғЯx“сөДХZСФТвО¶ЦшКІГҙ–|Оч����Ј¬ТтҙЛ‘—·ЁөДә¬БxКЗДЬүтұ»ИЛЦӘөАөДЎЈ
[2]ЛыЦёШҹ(zЁҰ)Т»Р©·Ё№ЩәНҢW(xuЁҰ)ХЯЦчҸҲ‘—·ЁөДә¬БxІ»ФЪУЪЖдОДЧЦ¶шКЗЖдҫ«ЙсөДУ^ьc(diЁЈn)�Ј¬ЛыХfЈәЎ°Я@Р©ИЛәЬЙЩҢў‘—·ЁөДә¬БxјҜЦРУЪҫЯуw—lОДөДХZСФЙП¶шКЗёь¶аөШкP(guЁЎn)ЧўУЪуw¬F(xiЁӨn)ФЪ‘—·ЁЦ®ЦРөДЎ®ИЛоҗЧрҮА(yЁўn)өДУ^ДоЎҜ����Ј¬Я@·N·ЁҢW(xuЁҰ)·Ҫ·ЁҢ§(dЁЈo)ЦВБЛДіР©І»ҢӨіЈөДәНІ»РТөДҪY(jiЁҰ)Х“Ў���ЈЎұ
[3]ГЧЙӘЦёіцЈәЎ°‘—·ЁөДХZСФКЗҫЯуwөД�Ј¬ұШнҡөГөҪЧсКШ���Ў�����ЈЎұјҙК№ХZСФОДЧЦДЈәэРиТӘГчҙ_Ждә¬Бx���Ј¬ҪвбҢХЯРиТӘЧцөҪҪвбҢ•r(shЁӘ)ЦБЙЩЕc‘—·ЁЧФЙнөДОДұҫІ»ӣ_Н»���Ј¬Ў°Из№ыҢў‘—·ЁЧчһйТ»ӮҖ(gЁЁ)ҝХЖҝЧУ¶шФКФSГҝТ»ҙъ¶јҢўЖдјӨЗйЕcЖ«ТҠСbЯM(jЁ¬n)ЖдЦРЈ¬КЗОЈлU(xiЁЈn)өДЎұ��ЎЈ
[4]ҙу·Ё№Щәъ№ыЎӨІјИRҝЛЦёіцЈәЎ°ОТҢҺФё°СОТөДРЕСцҪЁБўФЪіЙОД‘—·ЁЧФЙнОДЧЦЦ®ЙП����Ј¬¶шІ»ФёҢўЯ@·NРЕСцҪЁБўФЪҫЯУРБчЧғРФәНјҙ•r(shЁӘ)РФөДӮҖ(gЁЁ)ИЛЕР”аөД№«ЖҪЦ®ЙПЎ�����ЈЎұ
[5]ҙу·Ё№ЩІјИRҝЛФшХfЯ^Јә‘—·ЁКЗЎ°ОТөД·ЁВЙКҘҪӣ(jЁ©ng)Ўұ��Ј¬ЛыЎ°ХдТ•‘—·ЁөДГҝТ»ӮҖ(gЁЁ)ЧЦ��Ј¬ҸДөЪТ»ӮҖ(gЁЁ)ЧЦөҪЧоәуТ»ӮҖ(gЁЁ)ЧЦЎӯЎӯОТӮҖ(gЁЁ)ИЛХJ(rЁЁn)һйҢҰ(duЁ¬)‘—·ЁЧоЭpОўЦ®ТӘЗуөДЧоРЎұілx¶јёРөҪұҜНҙ�����Ў�ЈЎұІјИRҝЛЧ·лSЙсКҘФӯОДөДФӯіхә¬БxЈ¬¶шҫЬҪ^іРХJ(rЁЁn)Я@Р©ФӯОДҝЙДЬлSЦш•r(shЁӘ)ҙъөДёДЧғ¶шёДЧғЎЈ
[6]
кP(guЁЎn)УЪ‘—·ЁҪвбҢКЗ·с‘Ә(yЁ©ng)®”(dЁЎng)МҪҫҝОДЧЦөДә¬БxЙП���Ј¬»щұҫЙПҙжФЪЦшИэ·NУ^ьc(diЁЈn)ЈәТ»·NКЗЦчТӘ·Ё№ЩІ»ТӘКЬОДЧЦә¬БxөДПЮЦЖ����Ј»өЪ¶ю·NКЗЦчҸҲ®”(dЁЎng)ОДЧЦөДә¬БxЗеію•r(shЁӘ)ЧрЦШОДЧЦөДә¬Бx����Ј¬Ц»УР®”(dЁЎng)ОДЧЦДЈәэ•r(shЁӘ)ІЕДЬҢўЕРӣQөДАнУЙҪЁБўФЪЖдЛыХэ®”(dЁЎng)АнУЙЦ®ЙПЈ»өЪИэ·NЦчҸҲә¬БxҫЯУРДі·NБҰБҝ��Ј¬іэ·ЗФЪ°l(fЁЎ)Йъӣ_Н»•r(shЁӘ)ДЬүтұ»ЖдЛыАнУЙЛщНЖ·ӯ��ЎЈө«КЗ���Ј¬Я@Иэ·NУ^ьc(diЁЈn)ұM№ЬҙжФЪЦшІо®җЈ¬ө«КЗҪФіРХJ(rЁЁn)ОДЧЦөДә¬БxКЗҪвбҢ‘—·Ё•r(shЁӘ)ЛщКЧПИҝј‘]өД���ЎЈ®…ҫ№‘—·ЁҪвбҢКЧПИКЗҢҰ(duЁ¬)‘—·ЁОДЧЦөДҪвЧx�Ј¬ӣ]УРҢҰ(duЁ¬)‘—·ЁОДЧЦөДАнҪвЕcҪвбҢ�����Ј¬әОЦ^‘—·ЁҪвбҢЈҝХэИзӣ]УРйҶЧxҲу(bЁӨo)јҲөДОДЧЦҫНІ»ДЬҪвбҢҲу(bЁӨo)јҲТ»ҳУ�����Ј¬ӣ]УРйҶЧx‘—·ЁОДұҫөДХZСФОДЧЦҫНІ»ДЬҪвбҢ‘—·Ё�����ЎЈӣ]УРә¬Бx»тТвБxөДОДЧЦКЗҹoУГөД�����ЎЈИз№ыФЪҝҙөҪ‘—·ЁөЪ¶ю—lРЮХэ°ёкP(guЁЎn)УЪЎ°right of the people to keep and bear armsЎұЯ@ҫдФ’•r(shЁӘ)����Ј¬Из№ыҢўЎ°armsЎұАнҪвһйИЛөДЙнуwЦ®Іҝ·ЦөДФ’Ј¬ҫНІ»ДЬңК(zhЁіn)ҙ_өШҪвбҢ‘—·ЁЛщЩxУиөД№«ГсіЦУРҳҢЦ§өДҷа(quЁўn)АыөДә¬Бx���ЎЈЛщТФ����Ј¬Ў°‘—·ЁОДЧЦөДә¬БxјҙК№І»КЗҪвбҢөДЧоҪKДҝөД���Ј¬ТІЦБЙЩКЗ‘—·ЁҪвбҢөДй_КјЎұ���ЎЈ
[7]И»¶ш��Ј¬Ңў‘—·ЁҪвбҢФVЦTУЪОДЧЦөДә¬БxЯ@Т»ГІЛЖәҶ(jiЁЈn)ҶОөДҶ–о}��Ј¬ЖдҢҚ(shЁӘ)л[ә¬Цшеe(cuЁ°)ҫCҸН(fЁҙ)лsөДҶ–о}���Ј¬Я@ҫНКЗЈәИз№ығHғH‘{Ҫи‘—·ЁОДЧЦөДЖХНЁә¬Бx»тХЯ№«й_ә¬БxЯM(jЁ¬n)РРҪвбҢЈ¬ҢўІ»ҝЙұЬГвөШіц¬F(xiЁӨn)ДіР©»ДЦҮөДҪвбҢ���ЎЈһйҙЛ�Ј¬ҫНРиТӘНЁЯ^ғr(jiЁӨ)ЦөЕР”а��ЎЈЛщТФҫНМбіцБЛТ»ӮҖ(gЁЁ)Ҷ–о}ЈәјҙМҪЗуОДЧЦөДә¬БxКЗ·сҫНДЬүтұЬГв·Ё№ЩөДғr(jiЁӨ)ЦөЕР”а�ЈҝұЬГвғr(jiЁӨ)ЦөЕР”аІ»КЗҢўҪвбҢҪЁБўФЪОДЧЦә¬Бx»щөA(chЁі)ЙПЦ®ОЁТ»АнУЙЈ¬¶шКЗФӯТвЦчБxХЯҸҠ(qiЁўng)Х{(diЁӨo)ОДЧЦә¬БxөДЦчТӘДҝөДЦ®Т»����ЎЈФӯТвЦчБxХЯөДДҝөДКЗ�Ј¬»щУЪҙ_ұЈЕРӣQөД№«ХэЎўәП·ЁЕc·Җ(wЁ§n)¶Ё¶шТӘЗу·Ё№ЩұШнҡұЈіЦЦРБўЈЁneutralЈ©��ЎЈИ»¶ш�Ј¬өЪТ»Ј¬ФӯТвЦчБxХЯЙхЦБТІІ»өГІ»іРХJ(rЁЁn)Ј¬Из№ыУЙ·ЁВЙЩxУиБЛ·Ё№ЩЧФУЙІГБҝөДҪвбҢҷа(quЁўn)�Ј¬ДЗГҙ·Ё№ЩөДғr(jiЁӨ)ЦөЕР”аКЗІ»ҝЙұЬГвөДЎЈГЧЙӘТІіРХJ(rЁЁn)Јә‘—·ЁІ»КЗТ»ГжзRЧУ���Ј¬ғHғHәҶ(jiЁЈn)ҶОөШХЫЙдіцХҫФЪЛьГжЗ°өДИЛөДЛјПләНУ^До�����Ј¬Тт?yЁӨn)йЎ°‘—·ЁІГЕРп@И»І»КЗТ»ӮҖ(gЁЁ)ҷC(jЁ©)РөөДЯ^іМ�����Ј¬ЛьРиТӘФVЦTУЪАнРФәНЧФУЙІГБҝ���ЎЈЎұ
[8]ЯBұ»ХJ(rЁЁn)һйКЗГАҮш(guЁ®)ұИЭ^ұЈКШөДБ_І®МШЎӨHЎӨІ©ҝЛ¶јіРХJ(rЁЁn)ЈәЎ°®”(dЁЎng)И»��Ј¬·Ё№ЩГҝТ»ҙОҢҸАн°ёјю¶јФЪДі·NіМ¶ИЙПұШнҡФм·Ё���Ј¬І»Я^Ц»КЗФЪРЎөДҝХП¶йgФм·ЁЎұ��ЎЈ
[9]Тт?yЁӨn)йФЪІ©ҝЛҝҙҒн����Ј¬Ў°·Ё№ЩөДЯm®”(dЁЎng)?shЁҙ)ДИО„?wЁҙ)І»КЗҷC(jЁ©)РөөДЎұЈ¬ЛыТэУГCardinal NewmanөДФ’ХfЈәЎ°ҡvК·І»КЗТ»·NҪМ—l»тҶ–ҙрКҪҪМУэ����Ј¬ЛьҪoИЛТФҪМУ–(xЁҙn)¶шІ»КЗТҺ(guЁ©)„tЎұЎЈ
[10]ҸД‘—·ЁОДұҫХZСФҒнҝҙ�����Ј¬Из№ыБў‘—ХЯ»тХЯЕъңК(zhЁіn)ХЯУыТФОҙҒнөД·Ё№ЩЧсХХЛыӮғЛщҙ_БўөДҳЛ(biЁЎo)ңК(zhЁіn)өДФ’���Ј¬ЛыӮғ‘Ә(yЁ©ng)®”(dЁЎng)•ю(huЁ¬)ҢўЯ@оҗҳЛ(biЁЎo)ңК(zhЁіn)ЧчіцГчҙ_ЕcҫЯуwөДұнЯ_(dЁў)��Ј¬ө«КЗЯzә¶өДКЗЛыӮғІўОҙЯ@ҳУЧц���ЎЈҢҚ(shЁӘ)лHЙПЈ¬ЛыӮғЦ®ЦРөДФS¶аИЛҢўЛыӮғөДУӣ‘ӣұЈіЦБЛіБД¬����Ј¬К№Ц®іЙһйБЛГШГЬЎЈЯ@·NіБД¬ХfГч���Ј¬Бў‘—ХЯКЗПЈНыЩxУиОҙҒн·Ё№ЩК№УГЧФјәөДҳЛ(biЁЎo)ңК(zhЁіn)¶шІ»КЗБў‘—ХЯөДҳЛ(biЁЎo)ңК(zhЁіn)өДҷа(quЁўn)БҰ����ЎЈБнНвТ»ӮҖ(gЁЁ)ҢҰ(duЁ¬)ҙЛҝЙДЬөДҪвбҢКЗ�����Ј¬лmИ»Бў‘—ХЯІ»•ю(huЁ¬)Н¬ТвҫЯуwөДҳЛ(biЁЎo)ңК(zhЁіn)����Ј¬ө«КЗәЬлyХfҫНЩқіЙҢўОҙҒнөД·Ё№ЩПЮЦЖУЪИОәОМШ„eөДҳЛ(biЁЎo)ңК(zhЁіn)ЙПЎЈЛщТФ�Ј¬јҙК№МҪЗуОДЧЦөДә¬БxЈ¬ТІІ»ДЬұЬГвЛщУРөДғr(jiЁӨ)ЦөЕР”а�����ЎЈөЪ¶ю����Ј¬‘—·ЁЦРөДТ»Р©ОДЧЦЛЖәхЦұҪУФКФS·Ё№ЩАыУГЛыӮғЧФјәөДғr(jiЁӨ)ЦөЕР”аЈ¬Ж©Из��Ј¬‘—·ЁөЪЛДРЮХэ°ёЦРөДЎ°·ЗХэ®”(dЁЎng)ЎұЈЁunreasonableЈ©�����ЎўөЪОеРЮХэ°ёЦРөДЎ°Хэ®”(dЁЎng)ЎұЈЁdueЈ©әНЎ°№«ХэЎұЈЁjustЈ©�ЎўөЪ°ЛРЮХэ°ёЦРөДЎ°Я^УЪЎұЈЁexcessiveЈ©әНЎ°ҡҲҝбЎұЈЁcruelЈ©����ЎўөЪҫЕРЮХэ°ёЦРөДЎ°ҷа(quЁўn)АыЎұЈЁrightsЈ©��ЎўөЪТ»РЮХэ°ёЦРөДЎ°РЕҪМЧФУЙЎұЈЁfree exerciseЈ©әНЎ°СФХ“ЧФУЙЎұЈЁfreedom of speechЈ©��ЎўөЪК®ЛДРЮХэ°ёЦРөДЎ°ЧФУЙЎұЈЁlibertyЈ©әНЎ°ЖҪөИЎұЈЁequalЈ©өИ�ЎЈ‘—·ЁЦРөДЯ@Р©ОДЧЦЛЖәхФКФS·Ё№ЩЦұҪУЯ\(yЁҙn)УГЛыӮғЧФјәөДөАөВЕР”аЈ¬ЛщТФЯ@Р©ОДЧЦөДҪвбҢҫНҹo·Ё»ШұЬ·Ё№ЩөДғr(jiЁӨ)ЦөЕР”а�����ЎЈөЪИэ���Ј¬ФЪНЖ·ӯЖХНЁөДә¬Бx»тХЯЯx“сОДЧЦөДҢЈҳI(yЁЁ)ә¬БxЙПТІҙжФЪғr(jiЁӨ)ЦөЕР”аЦ®ҝЙДЬ�����ЎЈЖ©Из1954ДкІјАК°ёҢҚ(shЁӘ)лHЙПҫНКЗЯ\(yЁҙn)УГРВөДғr(jiЁӨ)ЦөЕР”аНЖ·ӯБЛ1896ДкЖХИRОч°ёөДЎ°ЖҪөИө«ёфлxЎұөДЕРӣQФӯ„t�����ЎЈЛщТФ�Ј¬ОДЧЦөДә¬БxІ»КЗЕЕіэ¶шКЗРиТӘ·Ё№ЩөДғr(jiЁӨ)ЦөЕР”аЎЈ
¶ю�����ЎўБў‘—ХЯТвҲD
ФӯТвЦчБxХЯҪӣ(jЁ©ng)іЈФVЦTУЪЦЖ‘—ХЯөДФӯКјТвҲD(the intentions of the authors of the constitution)ФҮҲDұЬГв·Ё№ЩӮҖ(gЁЁ)ИЛөДғr(jiЁӨ)ЦөЕР”а���ЎЈЖ©ИзКЧПҜҙу·Ё№ЩӮҗҝьЛ№МШФЪ№«№ІҢW(xuЁҰ)РЈЖн¶\°ёЦРХfөАЈәЎ°ҷа(quЁўn)Аы·Ё°ёөДЖрІЭХЯЎўБў‘—ХЯЛщҙ_БўөДФӯ„tЖщҪсУРР§ТФҝШЦЖЦшОТӮғ����ЎЈИОәОұілxЛыӮғөДТвҲD¶јҢўК№ҙу‘—ХВөДУАәгРФФвөҪЖЖүДЈ¬Ц»ДЬҢ§(dЁЈo)ЦВТ»Р©·З·ЁЕРӣQөДіц¬F(xiЁӨn)�����Ў�����ЈЎұІ©ҝЛ1971ДкФЪЎ¶ЦРБўФӯ„tәНөЪТ»РЮХэ°ёөДДіР©Ҷ–о}Ў·Т»ОДЦРҫНХJ(rЁЁn)һйЈәҒнФҙУЪ‘—·ЁөДҷа(quЁўn)АыөДЦчТӘ·ҪКҪҫНКЗЎ°ҒнЧФУЪОДјю¶шІ»КЗҫЯуwғr(jiЁӨ)Цө��Ј¬ОДұҫ»тҡvК·ұнГч����Ј¬ЦЖ‘—ХЯҢҚ(shЁӘ)лHЙПТСҪӣ(jЁ©ng)ҢўЖдТвҲDЮD(zhuЁЈn)»ҜөҪБЛФӯ„tРФТҺ(guЁ©)„tЙПЎұЎЈ
[11]ҢҰ(duЁ¬)ТвҲDөДФVЗуіЈіЈЕcОДЧЦә¬БxөДМҪЗуВ“(liЁўn)ПөФЪТ»Жр����ЎЈ®…ҫ№��Ј¬‘—·Ё—lҝоХZСФЦ®ұіәул[ІШЦшБў‘—ХЯөДТвҲD�����ЎЈө«КЗ��Ј¬ОДЧЦөДә¬БxЕcБў‘—ХЯТвҲDУР•r(shЁӘ)КЗӣ_Н»өД�Ј¬ұҫҒнОДЧЦөДК№УГҫНКЗұнЯ_(dЁў)ТвҲD����ЎўЯ_(dЁў)өҪЖдДҝөДөД№ӨҫЯЈ¬ө«КЗ��Ј¬УРөДЗйӣrПВ•ю(huЁ¬)іц¬F(xiЁӨn)°ҙХХЖХНЁОДЧЦөДә¬Бx„tҝЙДЬЕcТвҲDЕcДҝөДІ»Т»ЦВЙх»тӣ_Н»���Ј¬ТтҙЛ��Ј¬ТвҲDұШнҡЕcОДЧЦөДә¬БxПа…^(qЁұ)„e�����ЎЈЖ©Из��Ј¬ГАҮш(guЁ®)‘—·ЁөДЦЖ¶ЁХЯөДТвҲDӣ]УРТӘҸUіэЕ«л`ЦЖ�Ј¬өЪК®ЛДРЮХэ°ёөДЦЖ¶ЁХЯөДТвҲDТІОҙҙтЛгИЎПы·NЧеёфлxЦЖ¶ИЈ¬ө«Ў°·ЁВЙөДЖҪөИұЈЧo(hЁҙ)ЎұЯ@Т»ОДЧЦХZСФФЪҪсМмөДҪвбҢҫНІ»ДЬЯwҫНЦЖ‘—ХЯөДТвҲD���Ј¬ЛьұШнҡлSЦшҡvК·өДЧғ»Ҝ¶шЧғ»Ҝ��ЎЈФЪЯ@АпЈ¬ТвҲDЕcОДЧЦ·ЦлxБЛ���ЎЈ
ТвҲDАнХ“јТЦчҸҲ®”(dЁЎng)·Ё№ЩҪвбҢ‘—·Ё•r(shЁӘ)�Ј¬Бў·ЁТвҲDҫНКЗұЬГвЛыӮғғr(jiЁӨ)ЦөЕР”аөДОЁТ»өДНҫҸҪ���ЎЈЧсСӯФӯКјТвҲDТІДЬүтК№‘—·ЁұЈіЦ·Җ(wЁ§n)¶Ё���Ј¬Тт?yЁӨn)йЯ^ИҘөДТвҲDІ»ДЬұ»®”(dЁЎng)ПВөД·Ё№ЩЛщёДЧғЎЈИ»¶ш���Ј¬ФVЦTТвҲDҝЙДЬ•ю(huЁ¬)УРҸҠ(qiЁўng)ИхЦ®·Ц�����Ј¬УРөДҸҠ(qiЁўng)Х{(diЁӨo)ИОәО‘—·ЁҪвбҢөДХэ®”(dЁЎng)РФөДО©Т»·Ҫ·ЁҫНКЗ·ыәПЦЖ‘—ХЯөДТвҲD�Ј»¶шИхТвБxЙПөДТвҲDЦчБxХЯФЪҪвбҢ‘—·Ё•r(shЁӘ)іэ·ЗУЪФӯіхТвҲDПаТ»ЦВЈ¬Из№ыіц¬F(xiЁӨn)ЕcФӯіхТвҲDПаӣ_Н»•r(shЁӘ)��Ј¬ҫНҢўЛыӮғөДЕРӣQҪЁБўФЪЖдЛыТтЛШЦ®ЙП����ЎЈ¶ш¶а”ө(shЁҙ)ТвҲDХ“ҪвбҢЦчБxХЯИФИ»ЦчҸҲБў·ЁХЯөДТвҲDКЗҪвбҢ‘—·Ё•r(shЁӘ)ұЬГв·Ё№Щғr(jiЁӨ)ЦөЯx“сөДОЁТ»·Ҫ·ЁЈ¬ЧсҸДФӯіхТвҲDДЬүтК№‘—·ЁұЈіЦ·Җ(wЁ§n)¶Ё���Ј¬Тт?yЁӨn)йЯ^ИҘөДТвҲDІ»ДЬУЙ¬F(xiЁӨn)ФЪөД·Ё№ЩЛщёДЧғ��ЎЈІ»Я^����Ј¬ЕcФVЦTОДЧЦөДә¬БxТ»ҳУ��Ј¬ҝҙЛЖәҶ(jiЁЈn)ҶОөШФVЗуТвҲDөДҶ–о}ТІл[ә¬ЦшФS¶аҸН(fЁҙ)лsөДҶ–о}�ЎЈКЧПИЈ¬ТвҲDКЗТ»·NРДАн о‘B(tЁӨi)���Ј¬¶ш‘—·ЁөДЖрІЭәНЕъңК(zhЁіn)КЗУЙұҠ¶аөДИЛ¶ш·ЗТ»ИЛНкіЙөД���Ј¬ҸД¶шҫНлyТФЕР”аДЗР©ИЛөДЛјПл���ЎўТвҲD»тРДАнКЗ‘—·ЁөДТвҲDЎЈЖдЦРЛщЙжј°өҪөДҶ–о}КЗЈәХlөДТвҲDКЗЗЎ®”(dЁЎng)?shЁҙ)Д����ЈҝФS¶аТвҲDАнХ“јТВ•·QҪвбҢ‘—·ЁөД—lҝо‘Ә(yЁ©ng)®”(dЁЎng)°ҙХХИЛГсөДТвҲDјҙЦЖ¶ЁХЯЈЁframersЈ©өДТвҲDЈ»ө«КЗ����Ј¬ҢўЦЖ¶ЁХЯөДОДЧЦЮD(zhuЁЈn)»Ҝһй‘—·Ё—lОДөДКЗЕъңК(zhЁіn)ХЯЈЁratifiesЈ©Ј¬ЛщТФКЗЕъңК(zhЁіn)ХЯ¶шІ»КЗЦЖ¶ЁХЯҙъұнЦш¶а”ө(shЁҙ)�����ЎЈЯ@ҳУҫН•ю(huЁ¬)К№ИЛӮғЮD(zhuЁЈn)ПтҸҠ(qiЁўng)Х{(diЁӨo)ЕъңК(zhЁіn)ХЯөДТвҲDЙП����ЎЈИ»¶ш�Ј¬Т»ө©ЮD(zhuЁЈn)Пт?qЁұ)ҰЕъң?zhЁіn)ХЯөДТвҲDМҪЗуЈ¬ПакP(guЁЎn)Ҷ–о}ҫН•ю(huЁ¬)лSЦ®іц¬F(xiЁӨn)ЈәЕъңК(zhЁіn)ХЯөДИЛ”ө(shЁҙ)ұҠ¶а�����Ј¬ТвҲD¶аҳУ»Ҝ�����ЎЈТ»Р©ЕъңК(zhЁіn)ХЯУЙУЪЩқіЙТ»Р©—lҝоН¶БЛЩқіЙЖұЈ¬ө«ЛыӮғҝЙДЬҢҰ(duЁ¬)ЖдЛыТ»Р©—lҝоІ»қMТв�����Ј»ТІУРөДЦ®ЛщТФН¶ЩқіЙЖұКЗТт?yЁӨn)йЛыӮғПЈНыҪвбҢХЯЧчҮ?yЁўn)ёс»тЧЦГжҪвбҢ���Ј¬¶шТ»Р©…sҝЙДЬЕcЦ®Па·ҙ�����ЎЈәОӣr��Ј¬УЙУЪҡvК·УӣдӣіЈіЈІ»НкХы»тПа»Ҙӣ_Н»¶шҹo·ЁёжФVФӯіхә¬БxКЗКІГҙ��Ј¬»тХЯКЗ·сКЗФӯіхә¬Бx���ЎЈ®”(dЁЎng)И»Ј¬Я@Р©Ҷ–о}өДҙжФЪІўІ»ДЬХfГчФVЗуТвҲDҫНКЗҹoТвБxөД���ЎЈ®”(dЁЎng)Бў·ЁХЯөДТвҲDКЗЗеіюөД•r(shЁӘ)әт�Ј¬ЯҖКЗТӘЧрЦШЛыӮғөДТвҲD�ЎЈН¬•r(shЁӘ)�����Ј¬УРөДТвҲDАнХ“јТЯM(jЁ¬n)¶шЦчҸҲіэ·З·ЁВЙЯ`ұіБЛГчҙ_өДБў‘—ТвҲD����Ј¬·с„tІ»ДЬНЖ·ӯ·ЁВЙ����Ј¬К№ЖдҹoР§ЎЈө«КЗ��Ј¬јҙК№ТвҲDКЗГчҙ_өД��Ј¬ө«КЗЛьӮғҝЙДЬ°ьә¬Цш¶аЦШТвҲD����ЎЈЖ©Из‘—·ЁөЪ14—lРЮХэ°ёкP(guЁЎn)УЪЎ°·ЁВЙЖҪөИұЈЧo(hЁҙ)ЎұЈЁequal protection of lawsЈ©��Ј¬ЕъңК(zhЁіn)ХЯөДДіР©ТвҲDКЗІ»Н¬өДЈәТ»Р©ЕъңК(zhЁіn)ХЯөДТвҲDКЗПЈНыЕ«л`«@өГёьҙуөДХюЦОЖҪөИ��Ј»¶шТ»Р©ЕъңК(zhЁіn)ХЯ„tПЈНыФцјУЛыӮғөДЙз•ю(huЁ¬)ЕcҪӣ(jЁ©ng)қъ(jЁ¬)ЖҪөИ����ЎЈТтҙЛ��Ј¬І»Н¬өДЕъңК(zhЁіn)ХЯҢҰ(duЁ¬)УЪПаН¬өДТ»Р©‘—·Ё—lҝоТІ•ю(huЁ¬)ҙжФЪІ»Н¬өДТвҲD�ЎЈБнНв�����Ј¬Из№ыФКФS·Ё№ЩҢўЖдЕР”аҪЁБўФЪ‘—·ЁөДійПуТвҲDЙП���Ј¬ДЗГҙЛыӮғҢўҫЯУРёьҙуөДҷа(quЁўn)БҰ����ЎЈЖ©Из‘—·ЁРтСФЛщҙ_БўөД‘—·ЁДҝөДЈәЎ°ҪЁБўТ»ӮҖ(gЁЁ)Үш(guЁ®)јТГАәГөДәНұҠҮш(guЁ®)���Ј¬ҙ_Бў№«ЖҪ��Ўўҙ_ұЈҮш(guЁ®)ғИ(nЁЁi)°ІИ«��ЎўМṩЖХұйөДёЈАы��Ўўҙ_ұЈОТӮғј°ЖдәуҙъөДЧФУЙәНРТё�ЈЎұ�ЎЈИз№ыФКФS·Ё№Щ°ҙХХЯ@Р©Т»°гөДТвҲDҪвбҢ‘—·ЁөДФ’Ј¬ДЗГҙҫНІ»ҝЙұЬГвөШК№·Ё№Щ“нУРБЛёьҙуөДЧФУЙІГБҝөДҷа(quЁўn)БҰ�����ЎЈЛщТФЈ¬јҙұгФVЦTТвҲD�����Ј¬ТІІ»ДЬұЬГв·Ё№ЩөДғr(jiЁӨ)ЦөЕР”аөДЯM(jЁ¬n)Ил�����ЎЈТ»ө©®”(dЁЎng)ТвҲDКЗ¶аЦШ•r(shЁӘ)��Ј¬·Ё№ЩҫН•ю(huЁ¬)ФЪДДТ»ӮҖ(gЁЁ)ёьДЬүтЯ_(dЁў)ЦВДҝөДТвҲDЦРЧчіцЯx“с���Ј»®”(dЁЎng)УцөҪІ»Н¬өДТвҲDіц¬F(xiЁӨn)ӣ_Н»•r(shЁӘ)��Ј¬Ж©ИзөЪТ»РЮХэ°ёЕcөЪК®ЛД—l°l(fЁЎ)Йъӣ_Н»•r(shЁӘ)����Ј¬ТІРиТӘғr(jiЁӨ)ЦөЕР”а����Ј»®”(dЁЎng)Т»Р©ӮҖ(gЁЁ)„eөДТвҲDЕc‘—·ЁТ»°гТвҲDПаӣ_Н»•r(shЁӘ)����Ј¬Лы•ю(huЁ¬)Яx“с‘—·ЁөДТ»°гТвҲDөИөИ��ЎЈТтҙЛ�����Ј¬ФӯіхТвҲDАнХ“ТІІ»ДЬұЬГвЛҫ·Ёғr(jiЁӨ)ЦөЕР”а���Ј¬ХэИзсRРӘ –1819ДкФЪMcCulloch v. Maryland°ёЛщЦёіцөДЈәЎ°‘—·ЁТвҲDіЦАm(xЁҙ)І»Н¬өД•r(shЁӘ)ҙъЈ¬Іў‘Ә(yЁ©ng)ҢҰ(duЁ¬)ИЛоҗёч·NІ»Н¬өДОЈҷC(jЁ©)��Ў��ЈЎұјИИ»‘—·ЁөДТвҲDКЗ‘Ә(yЁ©ng)ҢҰ(duЁ¬)ИЛоҗөДёч·NОЈҷC(jЁ©)�Ј¬¶шІ»Н¬•r(shЁӘ)ҙъөДОЈҷC(jЁ©)өДҪвӣQЮk·Ё„tҝЙДЬКЗІ»Т»ҳУөДЈ¬Я@ҫНРиТӘЯ\(yЁҙn)УГІ»Н¬•r(shЁӘ)ҙъөДғr(jiЁӨ)ЦөЕcҪӣ(jЁ©ng)тһ(yЁӨn)ЕР”а��ЎЈ
Иэ����ЎўЛҫ·ЁЕРАэ
іэБЛФVЗуФӯКјә¬БxЕcТвҲDНвЈ¬·Ё№ЩҪвбҢ‘—·Ё•r(shЁӘ)ЯҖіЈіЈЧсСӯЛҫ·ЁЕРАэ(precedents set by past judges)��Ј¬јҙЧсСӯПИАэФӯ„tЎЈІ»Я^ЧсСӯПИАэФӯ„tІ»КЗӣ]УРКІГҙҶ–о}өД�Ј¬ҢҰ(duЁ¬)ДЗР©І»РЕИО·Ё№ЩөДИЛ¶шСФЈ¬ЧсСӯЛҫ·ЁЕРАэЛЖәхИұ·ҰХэ®”(dЁЎng)РФ��Ј¬Тт?yЁӨn)йЯ^ИҘөДЕРАэТІКЗДЗР©·ЗҪӣ(jЁ©ng)ЯxЕeіцҒнөД·Ё№ЩҢ‘өДТвТҠәНЦЖЧчөДЕРӣQ���Ј¬ЛыӮғөДҷа(quЁўn)НюЕcҪсМмөД·Ё№ЩТ»ҳУКЬөҪИЛӮғөДЩ|(zhЁ¬)ТЙ��ЎЈө«КЗІ»№ЬФхҳУ�����Ј¬ЧсСӯЛҫ·ЁПИАэЦБЙЩДЬүтЯ_(dЁў)ЦВИэӮҖ(gЁЁ)ДҝҳЛ(biЁЎo)ЈәТ»КЗК№·ЁВЙЧғөГёьјУ·Җ(wЁ§n)¶Ё�Ј»¶юЧсСӯЕРАэҙуБҝөДЕРӣQДЬүтёьјУУРР§өШЧчіц���Ј¬Тт?yЁӨn)й·Ё№ЩІ»ұШҢ?duЁ¬)ГҝТ»ӮҖ(gЁЁ)°ёјюТ»Т»ЧчіцЕРӣQ�Ј»ИэКЗЧсСӯЕРАэөД·Ё№ЩДЬүтұЬГвЛыӮғЧФјәөДғr(jiЁӨ)ЦөЕР”а��Ј¬Тт¶шДЬүтұЈіЦЦРБў�����Ј¬К№ЕРӣQёьјУҝНУ^�ЎЈ
И»¶ш�����Ј¬ЧсСӯЕРАэН¬ҳУ•ю(huЁ¬)ҙжФЪТФПВИэӮҖ(gЁЁ)Ҷ–о}ЈәЖдТ»КЗЕРАэөД…^(qЁұ)„eјјРg(shЁҙ)ЎЈЧсСӯПИАэФӯ„t���Ј¬ТАХХЕРАэЯM(jЁ¬n)РРІГӣQ�Ј¬ұШнҡІЙИЎ…^(qЁұ)„eјјРg(shЁҙ)ЈЁthe technique of distinguishingЈ©���Ј¬јҙҢўТФЗ°өД°ёјюКВҢҚ(shЁӘ)ЕcРВіц¬F(xiЁӨn)өД°ёјюКВҢҚ(shЁӘ)ЯM(jЁ¬n)РР…^(qЁұ)„e��Ј¬лmИ»°l(fЁЎ)¬F(xiЁӨn)ғЙӮҖ(gЁЁ)З°әуІ»Н¬өД°ёјюөДКВҢҚ(shЁӘ)Іо®җКЗИЭТЧөД��Ј¬ө«КЗИзәОХ“ЧCТт?yЁӨn)йІо®җ¶шҢ?dЁЈo)ЦВЕРӣQөДІ»Н¬ТФј°ҪвбҢДҝЗ°°ёјюЛщЧчіцөДІ»Н¬УЪПИАэөДҪY(jiЁҰ)Х“өДХэ®”(dЁЎng)РФ����Ј¬…sКЗІ»ИЭТЧөД��ЎЈПаЛЖөД°ёјюЧчПаЛЖөШМҺАн����Ј¬І»Н¬өД°ёјюЧчІ»Н¬өДМҺАнЈ¬Я@КЗЧсСӯПИАэөДәЛРД���Ј¬ө«Ҷ–о}КЗДДР©°ёјюКЗПаЛЖөД���Ј¬ДДР©КЗІ»Н¬өД°ёјю�����Ј¬КЗРиТӘ·Ё№ЩӮҖ(gЁЁ)ИЛөДғr(jiЁӨ)ЦөЕР”аөД�����ЎЈҙу·Ё№ЩЛ№ҝЁАпҒҶЦёіцЈәЖХұй·ЁКЗУЙ·Ё№Щ°l(fЁЎ)Х№¶шҒн��Ј¬Ў°ЖХНЁ·Ё·ЁФәөД·Ё№ЩҫЯУРғЙҙу№ҰДЬЈәТ»КЗҢў·ЁВЙЯmУГөҪКВҢҚ(shЁӘ)Ц®ЦР����Ј¬ЛщУРөДІГЕРХЯ¶јЯ@ҳУЧц�����Ј»өЪ¶юӮҖ(gЁЁ)№ҰДЬТІКЗЧоЦШТӘөДТ»ӮҖ(gЁЁ)№ҰДЬҫНКЗФм·ЁЎұ����ЎЈ
[12]И»¶шЈ¬ЖХНЁ·Ё·ЁФә·Ё№ЩФм·ЁөДТ»ӮҖ(gЁЁ)Ҫ^ҢҰ(duЁ¬)З°МбҫНКЗЧсСӯПИАэ�Ј¬Л№ҝЁАпҒҶХJ(rЁЁn)һйЈәЎ°ӣ]УРЯ@ҳУөДФӯ„t�����Ј¬ЖХНЁ·Ё·ЁФәҢўІ»ДЬФмИОәОЎ®·ЁВЙЎҜЎұ�����ЎЈ
[13]ЛщТФЈ¬ЧсСӯПИАэФӯ„tКЗЗ°Мб�����Ј¬¶шФм·ЁІ»Я^КЗҢҰ(duЁ¬)ЕРАэөДРЮп—РФФцМн��ЎЈЖд¶юКЗҝЙДЬ•ю(huЁ¬)УцөҪТ»Р©РВөД°ёјю¶шҹoПИАэЧсСӯөДЗйӣr�����Ј¬ФЪҙЛЗйӣrПВ��Ј¬®”(dЁЎng)И»ёьРиТӘТАЩҮУЪ·Ё№ЩөДғr(jiЁӨ)ЦөЕР”а����ЎЈЖ©ИзЈ¬1965ДкЧоёЯ·ЁФәФЪGriswold v. Connecticut °ёЦРкP(guЁЎn)УЪЎ°л[ЛҪҷа(quЁўn)ЎұөДҪвбҢ�Ј¬ҫНКЗФЪҹoПИАэөДЗйРОПВЯ\(yЁҙn)УГ·Ё№ЩөДЦчУ^ғr(jiЁӨ)ЦөЕР”аЧчіцөД��Ј¬·ЁФәФЪФ“°ёЦРөЪТ»ҙОҙ_ХJ(rЁЁn)БЛ‘—·ЁРФл[ЛҪҷа(quЁўn)�����ЎЈөАёсАӯЛ№ФЪ¶а”ө(shЁҙ)ЕРӣQТвТҠЦРРы·Q�Ј¬·ЁФәҢҰ(duЁ¬)‘—·ЁөЪЛДРЮХэ°ёәНөЪОеРЮХэ°ёөДёч·NҪвбҢ„“(chuЁӨng)ФмБЛЎ°л[ЛҪЎұөДоI(lЁ«ng)УтәНЎ°л[ЛҪЎұөДҷа(quЁўn)Аы����ЎЈН¬ҳУЈ¬1973ДкІ®ёс·ЁФәФЪБ_ТБ°ёЦР„“(chuЁӨng)ФмРФұЈЧo(hЁҙ)БЛӢDЕ®өДЎ°үҷМҘҷа(quЁўn)Ўұ���ЎЈЖдИэКЗНЖ·ӯПИАэ•r(shЁӘ)РиТӘғr(jiЁӨ)ЦөЕР”а�����ЎЈТӘНЖ·ӯөДПИАэЕc¬F(xiЁӨn)ФЪЛщҙэМҺАнөД°ёјюМҺУЪІ»Н¬өДҡvК·•r(shЁӘ)ЖЪ�Ј¬¶шІ»Н¬өДҡvК·•r(shЁӘ)ЖЪ��Ј¬УЙИЛӮғЛщМҺөДОпЩ|(zhЁ¬)Йъ»о—lјюІ»Н¬��Ј¬УЙҙЛТІӣQ¶ЁөДИЛӮғөДЙз•ю(huЁ¬)ТвЧR(shЁӘ)РО‘B(tЁӨi)ЕcөАөВғr(jiЁӨ)ЦөУ^КЗІ»Н¬өД����ЎЈұM№ЬТФЗ°ЛщЧчіцөДЕРАэҝЙДЬФЪ®”(dЁЎng)•r(shЁӘ)ҝҙҒнҫЯУРЖдХэ®”(dЁЎng)РФ���Ј¬ө«КЗлSЦш•r(shЁӘ)ҙъөД°l(fЁЎ)Х№ЯM(jЁ¬n)ІҪЕcИЛӮғөАөВғr(jiЁӨ)ЦөУ^өДЧғЯwЈ¬Я^ИҘұ»Т•һйХэ®”(dЁЎng)?shЁҙ)Д�Ј¬ҪсМмҫНҝЙДЬІ»ұ»ҪУКЬЎЈОЦӮҗ·ЁФәФ?FONT face="Times New Roman">1954ДкІјАК°ёЦРҫНХfЯ^ЈәЎ°ОТӮғҹo·Ё°С•r(shЁӘ)зҠ“Ь»ШөҪ1868ДкөЪК®ЛД—lРЮХэ°ёНЁЯ^өД•r(shЁӘ)әт���Ј¬ЙхЦБ“Ь»ШөҪ1896ДкЖХИRОч°ёЕРӣQЧчіцөД•r(shЁӘ)әт����Ў�����ЈЎұТтҙЛ�����Ј¬ІјАК°ёІўӣ]УРЦұҪУРыІјЖХИRОч°ёЕРӣQөДҡvК·Хэ®”(dЁЎng)РФ�Ј¬¶шЦ»КЗҸҠ(qiЁўng)Х{(diЁӨo)Хf�����Ј¬‘—·ЁөДә¬БxлSЦшЧғ»ҜБЛөДЗйӣr¶шЧғ»Ҝ���ЎЈЧоДЬХfГчЯ@Т»Ҷ–о}өДКЗ1937ДкБ_Л№ёЈРВХюЗ°әуөДЧғ»Ҝ����Ј¬1937Дк‘—·ЁёпГьЦ®З°Ј¬ЧоёЯ·ЁФәөДғr(jiЁӨ)ЦөУ^ЕcёпГьәуөДғr(jiЁӨ)ЦөУ^јҙұгбҳҢҰ(duЁ¬)Н¬ҳУөДҶ–о}�Ј¬ЧчіцөДғr(jiЁӨ)ЦөЕР”а…sҪШИ»Па·ҙЈ¬јҙТФЧФУЙЯM(jЁ¬n)ІҪөДғr(jiЁӨ)ЦөУ^ИЎҙъБЛұЈКШЦчБxөДғr(jiЁӨ)ЦөУ^��ЎЈТтҙЛ���Ј¬ЙПКцИэӮҖ(gЁЁ)Ҷ–о}���Ј¬ҹoХ“КЗ…^(qЁұ)„eјјРg(shЁҙ)ЎўНЖ·ӯПИАэЯҖКЗҹoПИАэҝЙЧсКШөДЗйӣr�����Ј¬¶јЧоҪKлxІ»й_·Ё№ЩөДғr(jiЁӨ)ЦөЕР”а�����ЎЈ
ЛД����Ўўғr(jiЁӨ)ЦөЕР”а
ХэИзОТӮғЛщ·ЦОцөД����Ј¬ҹoХ“ЙПКцДЗ·NЗйӣr�����Ј¬ҝӮ•ю(huЁ¬)Йжј°өҪ·Ё№ЩөДғr(jiЁӨ)ЦөЕР”а(value judgements)����ЎЈЯ@ЦчТӘКЗТт?yЁӨn)йИОәОҪвбҢ¶јКЗ·Ё№ЩөДӮҖ(gЁЁ)ИЛҪвбҢЈ¬¶ш·Ё№ЩӮҖ(gЁЁ)ИЛКЗИЛ¶шІ»КЗЙс��Ј¬¶шИОәОИЛ¶јКЗЙз•ю(huЁ¬)кP(guЁЎn)ПөөДҝӮәН��Ј¬ұ»Йз•ю(huЁ¬)»ҜөД·Ё№ЩұШИ»Һ§ЦшЯ@ӮҖ(gЁЁ)Йз•ю(huЁ¬)ҪoЛыЛЬҫНөДғr(jiЁӨ)ЦөЗ°ТҠ��Ј¬¶ш·Ё№ЩФЪҪвбҢ·ЁВЙ•r(shЁӘ)„tҹoТЙҺ§ЦшЖдғr(jiЁӨ)ЦөЕР”а����Ј¬Я@КЗХlТІҹo·Ё”[Г“өД¬F(xiЁӨn)ҢҚ(shЁӘ)�ЎЈТтҙЛЈ¬Ц»ТӘКЗҢҰ(duЁ¬)ОДЧЦХZСФөДҪвбҢ����Ј¬ҹoХ“ОДҢW(xuЁҰ)��ЎўҡvК·��ЎўХЬҢW(xuЁҰ)ҪвбҢ����Ј¬ЯҖКЗ·ЁВЙҪвбҢ»т‘—·ЁҪвбҢ�����Ј¬ҪвбҢХЯұШИ»•ю(huЁ¬)ҢўҪвбҢҪЁБўФЪғr(jiЁӨ)ЦөЕР”аЦ®ЙП�ЎЈкP(guЁЎn)жIКЗЈ¬Я@·Nғr(jiЁӨ)ЦөКЗ·с·ыәПИЛоҗөДХыуwғr(jiЁӨ)ЦөәНЙз•ю(huЁ¬)ЯM(jЁ¬n)ІҪөДғr(jiЁӨ)ЦөУ^��ЎЈ
јИИ»·Ё№ЩөДҪвбҢҝӮ•ю(huЁ¬)Һ§УРЖдғr(jiЁӨ)ЦөЕР”а���Ј¬ДЗГҙҫН‘Ә(yЁ©ng)®”(dЁЎng)МҪҫҝЯ@·Nғr(jiЁӨ)Цө‘Ә(yЁ©ng)®”(dЁЎng)КЗКІГҙғr(jiЁӨ)Цө�ЈҝКЗөАөВғr(jiЁӨ)ЦөЯҖКЗЦЖ¶Иғr(jiЁӨ)Цө�����Ј¬»тХЯКЗҪӣ(jЁ©ng)қъ(jЁ¬)АыТжғr(jiЁӨ)Цө���ЎЈІ»Я^��Ј¬лmИ»ҙу¶а”ө(shЁҙ)·Ё№Щ•ю(huЁ¬)Яx“сөАөВғr(jiЁӨ)Цө�Ј¬ө«ТІУРөДФVЦTУЪҫЯуwөДЦЖ¶Иғr(jiЁӨ)Цө»тХЯР§ВКғr(jiЁӨ)ЦөЎўҪӣ(jЁ©ng)қъ(jЁ¬)ғr(jiЁӨ)Цө�ЎЈ®”(dЁЎng)И»Ј¬Т»ө©Яx“сБЛөАөВғr(jiЁӨ)Цө��Ј¬ЖдУ°н‘•ю(huЁ¬)ёьҙу��ЎўёьҸV·әР©�����ЎЈҫЯуw¶шСФ���Ј¬өАөВғr(jiЁӨ)ЦөөДУ°н‘ұн¬F(xiЁӨn)ФЪЈәТ»КЗҹoХ“·Ё№ЩҢўЖдҪвбҢҪЁБўФЪОДЧЦөДә¬Бx�ЎўТвҲDЯҖПИАэ»щөA(chЁі)ЙП���Ј¬·Ё№ЩЯҖКЗФVЗуөАөВғr(jiЁӨ)ЦөЈ»¶юКЗФЪҫЯуw°ёјюЦРҙ_¶ЁОДЧЦөДә¬Бx��ЎўТвҲDЯҖКЗЕРАэ�����Ј¬ТІ•ю(huЁ¬)Я\(yЁҙn)УГөАөВғr(jiЁӨ)ЦөЕР”аЈ»ИэКЗ®”(dЁЎng)МҪЗуОДЧЦә¬Бx����ЎўТвҲDәНЕРАэІ»ДЬЯ_(dЁў)өҪБоИЛқMТвөДҪвбҢҪY(jiЁҰ)Х“•r(shЁӘ)Ј¬•ю(huЁ¬)Я\(yЁҙn)УГөАөВЕР”а�����ЎЈЛДКЗ®”(dЁЎng)ҪвбҢЎ°ОҙБРЕeөДҷа(quЁўn)АыЎұ—lҝо•r(shЁӘ)��Ј¬ТІұШнҡТАЩҮөАөВЕР”а�����Ў����ЈҝЙТФХfЈ¬·Ё№ЩөДөАөВғr(jiЁӨ)Цөҹo•r(shЁӘ)І»ФЪ�ЎўҹoМҺІ»ФЪЎЈ¶шЕcЦ®ПалSөДҶ–о}КЗЈә‘Ә(yЁ©ng)®”(dЁЎng)ФVЦTУЪДДТ»·NөАөВАнХ“��ЈҝУР»щ¶ҪҪМөДөАөВ����Ўў№ҰАыЦчБxөДөАөВ���ЎўӮҖ(gЁЁ)ИЛҷа(quЁўn)АыЦБЙПөДөАөВЎўЯҖУРБ_ –Л№өДЦЖ¶ИөАөВөИөИ�����ЎЈ
ҝӮЦ®�����Ј¬НЁЯ^ТФЙП·ЦОцҫНДЬ°l(fЁЎ)¬F(xiЁӨn)���Ј¬‘—·ЁҪвбҢ•ю(huЁ¬)ТАЩҮУЪёч·NІ»Н¬өДАнУЙЈәОДЧЦөДә¬Бx���ЎўБў‘—ХЯТвҲDЎўЕРАэТФј°ғr(jiЁӨ)ЦөЕР”а�����ЎЈ¶шГҝТ»ӮҖ(gЁЁ)АнУЙЧФЙн¶јКЗҸН(fЁҙ)лsөД���Ј¬ЙхЦБЕcЖдЛыАнУЙПа»ҘҪ»Іж»тХЯЦШҜB»тХЯӣ_Н»Ј¬ТтҙЛәЬлyҢўЛщУРөДТтЛШ?cЁўi)nәПЖрҒніЙһйТ»ӮҖ(gЁЁ)И«ГжөДЎўғИ(nЁЁi)ФЪәНЦCөДҪвбҢАнХ“��ЎЈЧоәГөДЯx“с®”(dЁЎng)И»КЗПЈНыҢўЕРӣQДі·NАнУЙ»тТтЛШЦ®ЙП�Ј¬¶шҶ–о}КЗФЪТ»Р©°ёјюЦРҶОӘҡ(dЁІ)Я\(yЁҙn)УГёч·NТтЛШЦРөДДіӮҖ(gЁЁ)ТтЛШЈ¬ЛЖәх¶ј•ю(huЁ¬)®a(chЁЈn)ЙъІ»ҝЙҪУКЬөДҪY(jiЁҰ)№ы�����ЎЈЛщТФФЪёч·NТтЛШЦРЯM(jЁ¬n)РРҪвбҢөДЕЕРтҝЙДЬКЗұШТӘөДЈәЖ©Из����Ј¬КЧПИҝј‘]ОДЧЦөДә¬БxЈ»ЖдҙО����Ј¬®”(dЁЎng)ОДЧЦөДә¬БxІ»ҙ_¶Ё•r(shЁӘ)Яx“сМҪЗуТвҲDЈ»ФЩҙО�Ј¬Из№ыә¬БxЕcТвҲD¶јІ»Гчҙ_•r(shЁӘ)Ј¬ҫНФVЗуғr(jiЁӨ)ЦөЕР”а��ЎЈ |